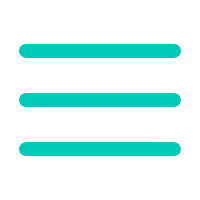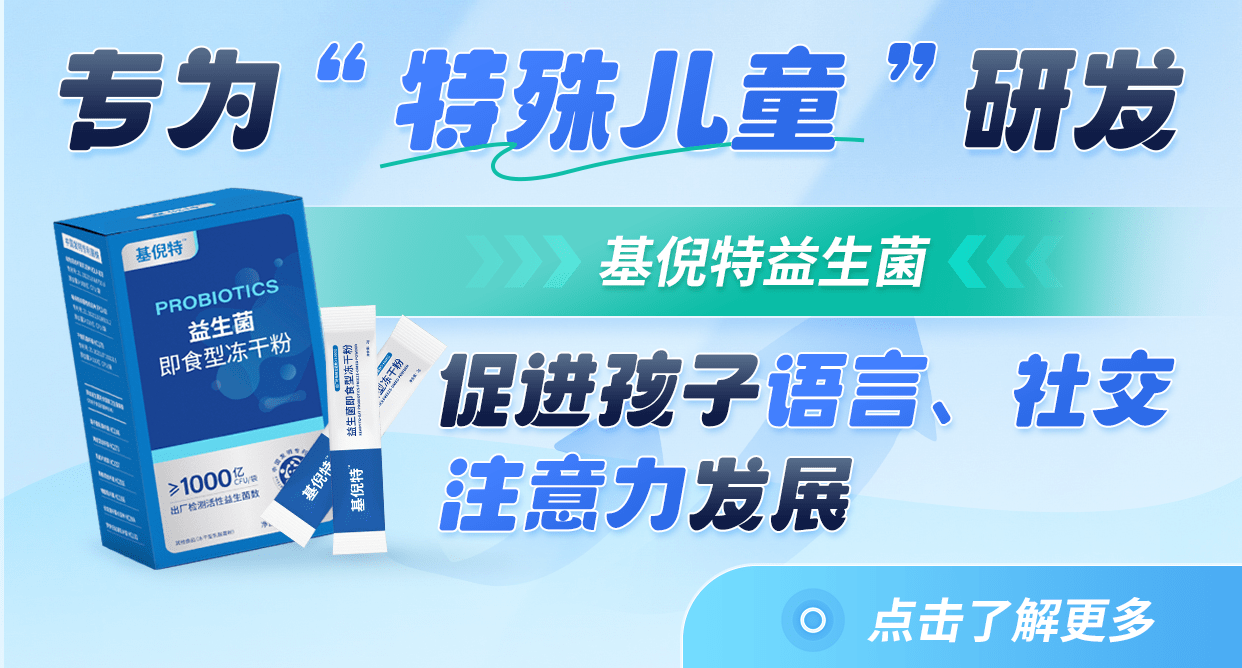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我的父母发现我的成长和两个姐姐非常不一样:我总是哭个不停,而且没法安抚。当我被抓起来的时候,我总是让我的双手在身边晃动着。
在我满一岁之前,我遭遇了一次严重的耳朵和喉咙感染,还对医生处方的抗生素严重过敏,以至于生命 垂危。在做了一大堆听力测试后,我父母被告知我可能聋了。几个月后,我似乎越来越与世隔绝,更加 沉迷于我自己的世界中去了。我不再对叫我的名字有反触。我对发生在我周围的景象和声音浑然不觉。我对身边很大的噪音充耳不闻却对隔壁房间几不可闻的声音着迷。

我丧失了对他人的兴趣,却能长时间地对着一些不动的物体呆若木鸡,比如盯着一支笔,墙上的一个记号甚至我自己的手看上老半天。我不想被触碰和拥抱。
我一言不发(甚至也不哭,不闹,不指,不做任何交流),进入了一种完全“静音”的状态,与我之前马 拉松式的大哭大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然后发生了一些让人吃惊的事:我痴迷于最简单的重复动作,比如在地板上转碟子一转就是几个钟头, 前后摇摆身体,在眼前不停地摇晃双手。
随着我情况的恶化,我父母带我看了无数专家,试图找出问题的原因所在。做测试,敲铅笔,摇头,然 不久,我被确诊为重度自闭症, 我的父母被告知我的智商低于30。对于一个毁灭性的诊断来说,最可怕的并不是诊断本身,而是对今后的预测——父母被告知了所有他们的孩子无法完成的事情。
像很多当今的父母一样,我的父母被告知这些预测都是板上钉钉的。我永远也无法说话或者用任何有意 义的方式交流了,我永远也不会对人比对物更感兴趣,我永远无法走出孤独变得“正常”。还有,我永远 无法上大学,有工作和打棒球。我永远无法恋爱、开车和写诗。我可能有一天会自己穿衣吃饭,但这就是我能力的上限了。焦急地寻找办法的父母最终却只得到冰冷的答案。他们在隧道中搜索着些许的光亮,却只得到了黑暗的预测。一而再再而三,他们告诉我父母要认命:自闭症是终身无法痊愈的。专家们向我父母说:当我长大成年了,我父母必须找一个永久的机构以便我得到适当的看护。
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我的父母发现我的成长和两个姐姐非常不一样:我总是哭个不停,而且没法安抚。当我被抓起来的时候,我总是让我的双手在身边晃动着。
在我满一岁之前,我遭遇了一次严重的耳朵和喉咙感染,还对医生处方的抗生素严重过敏,以至于生命 垂危。在做了一大堆听力测试后,我父母被告知我可能聋了。几个月后,我似乎越来越与世隔绝,更加 沉迷于我自己的世界中去了。我不再对叫我的名字有反触。我对发生在我周围的景象和声音浑然不觉。我对身边很大的噪音充耳不闻却对隔壁房间几不可闻的声音着迷。

我丧失了对他人的兴趣,却能长时间地对着一些不动的物体呆若木鸡,比如盯着一支笔,墙上的一个记号甚至我自己的手看上老半天。我不想被触碰和拥抱。
我一言不发(甚至也不哭,不闹,不指,不做任何交流),进入了一种完全“静音”的状态,与我之前马 拉松式的大哭大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然后发生了一些让人吃惊的事:我痴迷于最简单的重复动作,比如在地板上转碟子一转就是几个钟头, 前后摇摆身体,在眼前不停地摇晃双手。
随着我情况的恶化,我父母带我看了无数专家,试图找出问题的原因所在。做测试,敲铅笔,摇头,然 不久,我被确诊为重度自闭症, 我的父母被告知我的智商低于30。对于一个毁灭性的诊断来说,最可怕的并不是诊断本身,而是对今后的预测——父母被告知了所有他们的孩子无法完成的事情。
像很多当今的父母一样,我的父母被告知这些预测都是板上钉钉的。我永远也无法说话或者用任何有意 义的方式交流了,我永远也不会对人比对物更感兴趣,我永远无法走出孤独变得“正常”。还有,我永远 无法上大学,有工作和打棒球。我永远无法恋爱、开车和写诗。我可能有一天会自己穿衣吃饭,但这就是我能力的上限了。焦急地寻找办法的父母最终却只得到冰冷的答案。他们在隧道中搜索着些许的光亮,却只得到了黑暗的预测。一而再再而三,他们告诉我父母要认命:自闭症是终身无法痊愈的。专家们向我父母说:当我长大成年了,我父母必须找一个永久的机构以便我得到适当的看护。
时至今日,我仍然对我父母当年面对这样一个毁灭性的裁决时的抉择感到惊异。他们并不相信专家的判断,他们没有放弃我。相反,他们摒弃了那些可怕的预测。他们看着我的时候,想到的是这种可能而不是缺陷,心里不是充满恐惧而是充满希冀。
当我的父母开始真正了解我的世界,当他们反复用了无数的方法试图向我传达我是安全的,他们是爱我 的,他们是接受我的意思之后,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一个连接渐渐形成,我开始慢慢地、小心地从 我的特殊世界的面纱后窥视这个世界,我开始试探着加入他们。
随着我母亲经年累月的和我一起在地板上做我的那些“活动”,她成为了我的世界中的朋友,一条信任的 纽带出现了。她珍视每一次对视、每一次微笑、每一次他们期盼已久的连接,并为之欢呼雀跃。我每进 一小步她都无比兴奋。
随着我和父母的关系以及同其他人联系的加强,我的父母为我量身定制了一整套的疗育方案。他们帮助 我去增加我和他们以及其他人的连接,鼓励我和他们一起玩,看着他们,和他们一起大笑以及牵起他们 的手。他们为我日益增加的兴趣设计了一系列的互动游戏,比如动物游戏和飞机游戏。每一个回合,他们都采用呵护、鼓励和支持的方式,从不逼迫,总是邀请。
你能想象吗?他们从听到那些让人绝望的预测之后就开始了这样的试验,在我一点回应都没有的时候还 一直坚持要同我建立联系。
他们这样的做法饱受批评,学识渊博的专家们告诉我的父母他们这样“加入”我的活动会强化并增加我 的“问题行为”。这些专家们严厉的训斥我的父母选择了与他们推荐的行为矫正技术相反的方法,还斥责 他们抱有“虚幻的希望”,把自己的时间精力耗费在未经证实(或者叫刚刚创立)且没有成功希望的方法 上。家庭成员们也表示了质疑和焦虑,他们认为我父母在闭门造车,应该把我交给更有知识和经验的专 家去治疗。
别忘了,当时自闭症的疗育是一片蛮荒的处女地,根本没有新闻故事报道最新的疗育方案和谱系孩子家 庭的生活细节,也没有自闭症月刊可看。
我父母亲眼目睹了自闭症孩子被电击、被绑在椅子上、被放在黑监狱一样的屋子里等等,还被告知说这 是最新最好的疗育方案。
为了帮助我,他们孤独地走在了相反的路上。在得不到任何支持的情况下,他们一直支持着我。他们努力着,等着,坚持着和忍耐着。对未来茫然无知,也不要求我能够回报他们的爱、呵护、微笑和欢呼,他 们却给了我一切的机会。
经过三年半艰苦卓绝的努力,他们总算建立了一条从我的世界到他们世界的桥梁。于是一切都有了回报。
我在干预中,恢复得越来越好,我上小学,上大学,找工作,我变成了普通人。
最后我想说家庭干预对自闭症的康复会起到很大的作用,甚至于超过机构,希望自闭症患儿的家长不要放弃他们,我们的成长只是慢些费力些,我们一定不会辜负父母的努力,好好长大。